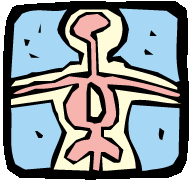 慢性病醫學的發展與一位老婦人錢德勒有密切的關係。她看到倫敦有許多老人得了中風、癱瘓、麻痺、失憶症,卻沒有一間醫院治療這種病。有一晚,她迫切地禱告:「上帝啊!幫助我!使我能在有限的時光裡,全心全力去補滿這樣的需要。」她奉獻所有並四處募捐。一八五九年十一月第一所神經疾病國際醫院成立,擔任首席大夫的就是布朗塞卡爾。
慢性病醫學的發展與一位老婦人錢德勒有密切的關係。她看到倫敦有許多老人得了中風、癱瘓、麻痺、失憶症,卻沒有一間醫院治療這種病。有一晚,她迫切地禱告:「上帝啊!幫助我!使我能在有限的時光裡,全心全力去補滿這樣的需要。」她奉獻所有並四處募捐。一八五九年十一月第一所神經疾病國際醫院成立,擔任首席大夫的就是布朗塞卡爾。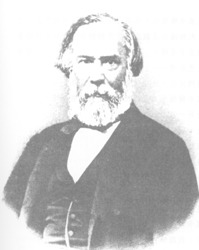 布朗塞卡爾
布朗塞卡爾遠離家園
一八三八年四月,法國巴黎來了風塵僕僕的一對母子。半年後,布朗塞卡爾進入巴黎醫科學院。當時法國亟需醫生,唸醫學院學費全免。
母親在巴黎,並沒有時間去逛名勝古蹟;她得沿街賣刺繡,用一針一線為孩子織成上進之路。法國的生活水準高,布朗塞卡爾在學校申請當大學一年級物理與化學課的助教。他後來寫道:,要把書唸懂的最好方法,就是自己唸完了再去教別人。,由於教別人實驗,他自己也成了一個實驗高手。他的老師馬丁馬格隆很器重他,讓他有一間個人用的實驗室。這成為他終身的必需裝備,他以後在任何地方,都有一間私人實驗室。
老人的贈款
醫學實驗室是學醫的地方,但也是危險的所在。一八四二年,他在實驗室清洗杯盤時割傷手指,因而感染杯中病毒,發病在家躺了幾星期。等到他病好了,照顧他的母親卻病倒了,病情急速惡化。任憑他的哭號與求助,母親離他走了;布朗塞卡爾成為最孤單的人。
夜裡他奔出巴黎街頭,邊跑邊哭,他成為無父無母、無兄弟姊妹的孤兒了。他搭上回模里西斯的船,返回家鄉;他失魂落魄地到處走,但是再也找不回母親了;只留下母親多年的心願:「我的兒子有一天會到法國唸醫學院」。布朗塞卡爾決心再回去唸書,也許再也救不回自己的母親,但是可以拯救天下人的母親。不過他沒有錢回巴黎。 在這山窮水盡之時,他收到一筆紐約寄來的錢。菲特斯是美國紐約聖司提反教會的牧師。他知道他有一位姪子因為船難,漂流到模里西斯島;也知道生了一個孩子之後,姪子就死了。菲特斯牧師從來沒有與模里西斯島的布朗家見過面,但是常為孤兒寡母禱告,並在死前立下遺囑,把他的微薄存款贈與布朗的兒子,並且附上許多勉勵孩子的信。這些微薄資助幫助布朗塞卡爾又能回到法國,布朗塞卡爾一生對這老牧師的恩情深感於心。 一八五二年布朗塞卡爾,以"脊椎神經生理的研究與試驗” 獲得醫學博士學位。畢業後,他一方面當醫生,一方面與醫學同好定期聚集,發表研究文章。
布朗塞卡爾的名氣漸響,歐美許多大學、醫院、學會都請他去演講。布朗塞卡爾把賺來的錢,不是送給病人,就是買實驗動物來進行實驗。他不擅外交,作風怪異。他寫道:「我要成為一個不發財的醫生,因為一個想發財的醫生,在醫學上不會有突破的發現。」別人笑他是,除了醫學什麼也不管的人。當時的巴黎醫生與現代醫生一樣,一見面就談最近又賺了多少錢?,布朗塞卡爾卻寫道:「一個人只要有一點小聰明就能賺大錢,賺大錢不算什麼聰明。由於我沒有把腦筋放在賺錢,導致我常左支右絀。」他在美國講學時,與福樂琪小姐結婚。他妻子婚後寫道:「法國人對信仰的輕忽,對嚴肅事情的嘲弄,對道德的討論多於實踐,令我感到這是一個陌生的國家。但是我的丈夫與周圍的人不同。我們兩人好像是浮華世界裡的一座孤島…. 布朗塞卡爾年輕時的苦難與不幸,使他對信仰有一種說不出的敬畏。
「霍亂!模里西斯霍亂流行! 」一八五四年春天巴黎的頭條新聞。法國的名醫沒有一個敢前往模里西斯,而島上的醫生卻是第一批向外移民逃命的人。布朗塞卡爾卻帶著妻子,回到模里西斯。他在聖瑪麗醫院晝夜不停地拯救病人。當他到達時,模里西斯的十八萬二千人,已經死了一萬八千人。每死一個人,當地土著就向天上發射一槍,希望趕走病魔。死的人太多了,每天槍聲砰砰響,像放煙火一樣。有一次,布朗塞卡爾給土著看病;那個病人突然嘔吐,把滿肚穢物吐到醫生的臉上。他立刻把穢物拭去,走到診療室外。他寫道:「我想這次我終於逃不過霍亂的感染了,我覺得病的陰影已經攀上心頭。我要逃回法國嗎?還是倒下來自憐一番……外面還有成排的病人向我求救,但是我要向誰求救呢?」
接著他做了一件不太合乎醫學的事:他端起身邊的咖啡,望著天,存著感謝的心喝下去,然後又接連地喝了幾杯。只有在他身旁的妻子,知道丈夫當這生死存亡之際在做什麼。
一八五四年十月,霍亂之疫在模里西斯消失了。布朗塞卡爾卻沒有倒下,他的信心成長了。他後來寫道:「醫學仍在一片模糊、彎曲的曠野上,在心裡一直燃燒著修直曠野之路的豪情壯志,本是來自天上的祝福。」
慢性病醫學的呼喚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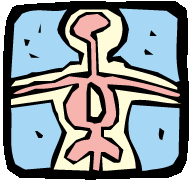 慢性病醫學的發展與一位老婦人錢德勒有密切的關係。她看到倫敦有許多老人得了中風、癱瘓、麻痺、失憶症,卻沒有一間醫院治療這種病。有一晚,她迫切地禱告:「上帝啊!幫助我!使我能在有限的時光裡,全心全力去補滿這樣的需要。」她奉獻所有並四處募捐。一八五九年十一月第一所神經疾病國際醫院成立,擔任首席大夫的就是布朗塞卡爾。
慢性病醫學的發展與一位老婦人錢德勒有密切的關係。她看到倫敦有許多老人得了中風、癱瘓、麻痺、失憶症,卻沒有一間醫院治療這種病。有一晚,她迫切地禱告:「上帝啊!幫助我!使我能在有限的時光裡,全心全力去補滿這樣的需要。」她奉獻所有並四處募捐。一八五九年十一月第一所神經疾病國際醫院成立,擔任首席大夫的就是布朗塞卡爾。
他不僅是傑出的醫生,也是一流的老師。一八六六年他寫了一篇:「給學生們的建議」其中寫到一個有志從事醫學的人所該具有的心志與認識:「從事醫生的工作是一生的辛勞,而且需要活在高度的自制之下。小組討論與學習,是醫學院最佳的學習方式。生物活體解剖是醫學必要的實驗,但是不要虐待動物。醫生對用藥需要有高度的警覺性,以免淪落成製藥市場的行銷人員。不要輕易接受任何理論,不管是多權威的人士說的,自己總要分析、明辨;對於一些難以理解的事情,不要太快就反對。」
不變的標竿
一八七八年他回到母校,擔任巴黎醫科學系系主任。他成為當時歐洲醫學的權威,以後陸續獲得無數的榮譽與獎狀,但是他寫道:「當成功與權力臨到我時,它們對我已沒有什麼意義。很多人一生忙於爭取權力或鞏固地盤,而看不見什麼才是他一生最重要的事。一個人愈到晚年,愈會發現即使在醫學界裡,也充滿了鬥拳打空氣、奔跑無定向的事。你丟掉的機會,別人會去揀﹔一度的名醫聲望,不曾永保門診的吸引力﹔一個成功的診所,所得的感謝並不長久﹔不受重視時,又會有職業性的酸葡萄心理,甚至退縮……因此,我仍遵行年輕時所立下的心願,不為這些容易改變的東西活著,而向那永不改變的標竿走下去。為此我寧願被外界批判,也不願傾聽外界給我的任何掌聲。」
他又寫道:「我永遠提醒自己,我是一個會犯錯的人,即使我已成為大學裡的權威,但是如果我錯了,我一定會公開認錯。一個醫生應該有自己的原則,有自己的個性﹔我一生沒有因醫學而發財,卻幫助許多人,這是我最引以為傲的事。」
布朗塞克爾死於,一八九四年四月一日,他只要求放幾朵模里西斯島的紫丁香與山茶花伴他長眠。
本文採至張文亮教授的《我聽見石頭在唱歌》一科學大師的求學 、戀愛與理念之(二)。